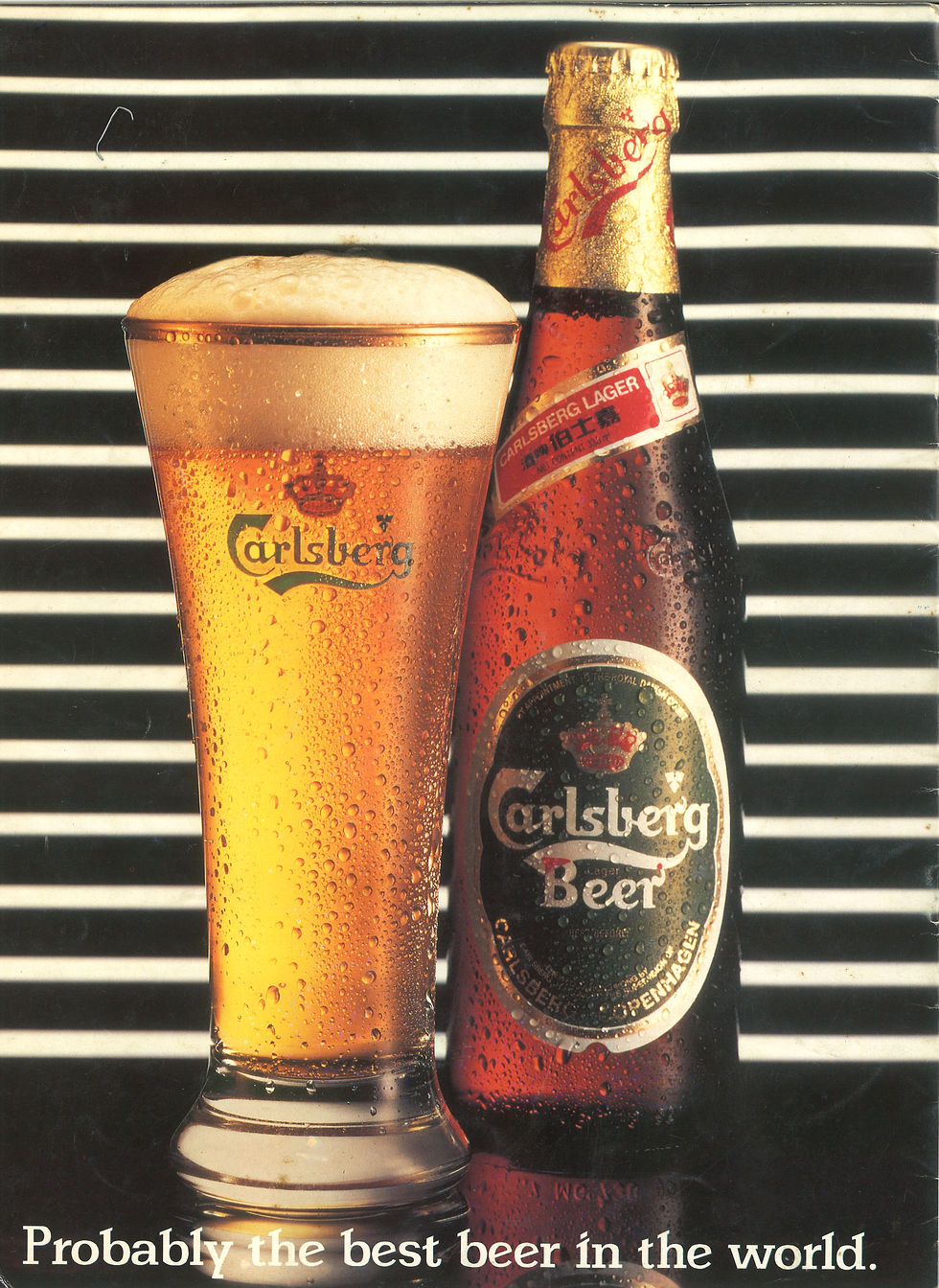「打棉胎」這項歷史悠久的傳統手藝,承載著上世紀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它也被稱為「彈棉」、「彈花」或「彈棉絮」,是一種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棉被製作技藝。二十世紀中的富善街街頭,便有一間名為「劉祥記」的傳統棉胎舖深入民心,即使早已結業,仍然讓大埔街坊記憶猶新。
傳統棉胎製作技藝
早在元朝時期,便有關於用木棉製作棉胎的記載。元代王禎的《農器圖譜集之三 · 纊絮門》中詳細描述了製作方法,其中南北方的做法各不同。古籍中記載了各種相關工具的使用,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木棉彈弓。這種弓⻑約四尺(約1.33 米), 上半部較⻑且呈彎曲狀,下半部較短且有勁,用繩弦繫住。工匠用弦彈射棉絮,能快速將棉花打成絮狀,效果顯著,充分展現了早期工匠的巧思。王禎更為《木棉彈弓》作詩一首:
主射由來彀此弓,豈知絃法有他功,
卻將一掬香綿朵,彈作晴雲滿座中。
到了二十世紀中的香港,打棉胎仍沿用類似的彈弓,⻑約兩米,使用牛筋製成弓弦。除此之外,「打」棉胎還需要用到木槌、梳孔的竹栻,以及一個特製的 木盤。在香港,打棉胎主要分成兩種方式:廣東的「地工」和客家的「企工」。 兩者的操作過程相似,只是前者將棉花放置地上操作;後者也稱「床工」, 將棉花放在床上,由工人背著工具「打」棉胎。整個製作流程大致如下:
首先是拍鬆棉花,然後用木槌敲擊「彈弓」的弦,使棉花更加鬆散。接著, 師傅會在鬆散的棉花上輕輕敲擊,名為「修面」,為了將棉花打成特定的形狀。
隨後,師傅會將棉胎稱重,並接著用「彈弓」輕彈四邊,讓棉花更加均匀,這個過程稱為「切邊」。之便是「壓花」,用疏孔的竹製工具壓在棉花上,固定形狀,然後進行「放綆」:每面棉胎一般需要放四層由棉紗撚成的「線綆」,橫、縱各一層,斜向再放兩層,使棉花不易鬆散。之後師傅會再調整「綆」的位置,稱為「執綆」。
最後,師傅會用一個特質的木盤用力「磨綆」,使棉花緊扣「線綆」,以防棉胎鬆散;接著便是將棉胎翻面,重複以上步驟,並加入「接邊」及「縫⻆」,棉胎才大功告成。


從人手一張到夕陽西下
這些工序不僅繁複,更需要耗費大量的體力。一幅約六斤重的棉胎,通常由兩位師傅合作,需時約兩個鐘才能完成。手工製作的棉胎,是當時普遍香港家庭裡的貴重物品,有時人們急需周轉,甚至會將棉胎拿去當舖換錢。在二十世紀初,香港報紙多次報導棉胎被盜或搶劫的案件,甚至出現因搶奪棉胎而釀成的慘案,可見當時生活的艱辛與物資的匱乏。戰後大量內地移⺠湧入香港,生活物資愈發緊拙,棉胎幾乎成為「奢侈品」。根據1962年冬季的報道,一名睡在⻄環北街的男子因爭搶棉胎而被刺傷。1964年李鄭屋村起火時,一小童本已逃出,卻想到天寒地凍便返回搶救棉胎,不幸被葬身烈火之中。寧可冒著被刺傷、被火燒的風險也要搶棉胎,可見一床暖和的棉胎在當時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大埔,曾有不止一家棉胎廠,而位於富善街口的「劉祥記」廣花棉胎更是不少街坊的集體記憶。棉胎師傅用彈弓在棉花堆裏彈啊彈,然後又魔法般地將其修成形, 再放上線綆,半天功夫,便成了一床暖和的棉胎。特別是秋涼或者遇到婚喪喜慶, 棉胎鋪的生意便會激增。
據1974年棉胎業商會的資料,當時全港約有50多處棉胎廠,每年生產約一萬多張棉胎。然而,隨著平價的大陸棉胎及尼龍等新材料的出現,傳統棉胎業逐漸式微。到了九〇年代,這項技藝也隨著製作師傅的年邁老去,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富善街口的棉胎店,現已成了水果店。打棉胎的手藝,亦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撰文:黃立妙
編輯:盧俊溢

2291 0238
免責聲明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香港賽馬會、其各自關聯公司或任何參與彙編此載內容或與彙編此載內容有關的第三方(統稱「馬會各方」)皆無就內容是否準確、適時或完整或使用內容所得之結果作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或聲明。任何情況下,馬會各方皆不會對任何人或法律實體因此載內容而作出或沒有作出的任何行為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2023-2026 © 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for Heritag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